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没有比利时人就读比利时最古老的大学。该机构成立于1425年,在法语中被称为Université天主教鲁汶,在荷兰语中被称为鲁汶Katholieke Universiteit te leuven,尽管它拥有丰富的遗产和国家象征价值,但它已经不再存在。与法国许多地方一样,讲beplay体育官网电脑板法语的瓦隆人长期以来在该机构享有特殊地位,尽管鲁汶位于讲荷兰语的弗兰德斯地区,但他们控制着该机构的管理。受够了,佛兰德学生要求大学纠正历史上的不平等,最终优先考虑讲荷兰语的大多数学生。
这个机构的派系接缝处已经四分五裂,只有从中间分裂才能解决问题。这一划分最终需要在边境另一边修建一个新城镇Louvain-la-Neuve(法语中的“新鲁汶”)和一个新校园,距离这里只有大约40分钟的车程。但是,把图书馆的藏书分开——把统一的文化和共同的历史分开——可能比建造一座新城市更难。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当瓦隆尼亚新的Université鲁汶天主教(UCLouvain)正在建设时,鲁汶的图书馆是一个分裂的房子。在瓦隆人等待他们的新图书馆完工的时候,这座靠近比利时中心的历史建筑——距离佛兰德斯和瓦隆尼亚的边界大约18英里——现在暂时容纳了两个不同的图书馆,为两个不同的机构服务,分别为两个语言社区服务。学生、教师和员工“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没有在一起工作,”查尔斯-亨利·尼恩斯(Charles-Henri Nyns)说,他现在是鲁汶大学的首席图书馆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是鲁汶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正在进行分裂。他说,工作人员被指示只用一种语言帮助学生,而不是另一种语言——不回答用错误语言接近他们的学生。
决定你使用哪种语言的唯一因素是命运注定你是弗莱明人还是瓦隆人;因此,图书在两家机构之间的划分不是基于它们的语言或主题,而是主要基于它们自己的标签——它们的书架标记。

要不然如何分割这些不仅包含书籍,还包含历史本身的藏品呢?有些历史是值得骄傲的:16世纪,伊拉斯谟在这座城市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图书馆收藏着他的信件。这座建筑记录了低地国家对艺术和科学的贡献,记录了知识分子的运动,如荷兰人文主义和詹森主义。在一个以缺乏民族凝聚力而闻名的国家,图书馆似乎是能找到的最接近比利时统一的象征。
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悲惨而残酷的被洗劫只是重申了这种象征意义。1914年8月25日,德国军队点燃了图书馆,作为对鲁汶的集体惩罚的一部分,以报复所谓的狙击。根据佛兰德机构(KU Leuven)档案保管员马克·德瑞兹(Mark Derez)的研究,2000多所房屋被烧毁,248人死亡,“烧焦的纸碎片一直飘到周围的乡村”。
这座城镇成了联合起来对抗德国的军队的一个方便的宣传场所。德雷兹写道,在英国,一些船只甚至1914年出生的女婴都以鲁汶命名,如“鲁汶!“这是我们的战斗口号”成为了一次军事进行曲的名称。德雷兹写道,被烧毁的图书馆尤其令人痛心,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它的军事价值是合理的。它的形象帮助把这场战争从“政治-军事冲突”重新塑造成“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一方会肆意破坏文物,进行虚无主义的侵略。
Derez转述了一段轶事,可能是杜撰的,其中一个人的家在德国袭击中被烧毁,他试图向一位美国外交官描述大屠杀。他讲完了自己家庭的故事,但说到“bibliothèque”这个词时总是结结巴巴的,最后哭了起来。即使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它的讲述也说明了Derez的关键观察。“对文化商品的攻击,”他写道,“继续在人们的脑海中燃烧,并沉淀到集体记忆中。象征秩序最终战胜了个人悲剧。”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团结在图书馆周围,帮助比利时治愈战争的创伤。1928年,一些曾在战场上为比利时而战的佛兰德语学生抵制了新建图书馆的落成仪式,因为法兰西学院参与这个项目向他们表明了亲法语的偏见。德雷兹在一次采访中说:“法语被视为一种代表社会压力和傲慢的语言。”即使是德国人的愤怒也无法消除这种印象。(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再次袭击了该图书馆。)
1834年,随着比利时王国的建立,主教接管了这所大学,尽管大学位于讲荷兰语的佛兰德斯,但教学和行政几乎完全由法语主导。(唯一的例外是一门佛兰德文学课程。)鲁汶大学(KU Leuven)的历史学家路易斯·沃斯(Louis Vos)写道,他们感觉自己好像被忽视了一样,“把讲法语的同事视为贵族、势利、居高临下的资产阶级,他们仍然相信法语的优越性,因此拒绝学习荷兰语。”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佛兰德民族主义活动之后,该机构直到1911年才开始增加荷兰语课程。
到1936年,这所大学已经扩展到为学生提供完全的荷兰语课程,但这种扩张只会隔离这两个语言群体,使他们变得独立,而且明显不平等。沃斯说,上世纪60年代在这所大学读书时,同一个讲堂会连续两期讲授同一门课程:每种语言各上一节课。当学生们拖拖拉拉地进进出出时,他们会完全忽略彼此。尼恩斯说,20世纪70年代,当分裂正在进行时,瓦隆社区“就像一个犹太人区”;他能够结交一些佛兰德朋友,但这只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努力。与此同时,沃斯说,在鲁汶读书期间,他从未与说法语的人直接交谈过。
“认为比利时是双语国家的想法并不完全正确,”沃斯说。这种情况更接近于一种基于“真正敌意”的“自我选择的种族隔离”——当然,实行起来是不平等的。他回忆说,讲法语的学生可以使用很好的实验室,而佛兰德语的学生则被下放到地下室,尽管学生人数更多,但他们学习科学的预算更少。

因此,佛兰德人的抗议活动持续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其中一些是暴力的)。学生们高唱“我们一定能战胜”,并高呼“Walen buiten!””——“龙人!——直到最后,每个群体都必须由自己独特的机构来服务。虽然大部分藏书——两次遭到暴力袭击——必然是新的,但争夺图书馆馆藏的斗争仍然是症结所在;这座图书馆仍然代表着悠久而充满活力的历史。除了伊拉斯谟的信件,这些藏品还包括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以及最古老的匈牙利语手稿——这是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对一战的赔款的一部分。Derez回忆起一位同事在自己的卧室里藏了一本罕见的15世纪祈祷书(货架标记A12),目的是为了不让瓦隆人看到,这样他们就不会把它带到新的城镇
管理人员最终确定了一些武断的基本规则,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是最公平的。如果可以联系到作品的捐赠者,捐赠者可以选择作品的去向——如果同一作品有多个版本,每个机构将保证至少有一个副本。但大多数作品只是按书架标记进行了划分:奇数留在鲁汶,偶数留在新鲁汶。这是一种奇怪的、平淡无奇的解决根本情感冲突的方法。随着瓦隆的学生和教师——据尼恩斯回忆,他们“失去了家园”——书籍穿过边境,涌入了这个新的prop大学城,据沃斯说,当时这里只有开阔的田野。
如今,这两个机构关系平静,偶尔举行仪式,并定期在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尼恩斯补充说,法律专业的学生通常会在另一所学校学习6个月,因为许多比利时律师都需要掌握双语。但这是冷和平。德雷兹说,目前两地的学生很少说彼此的语言,瓦隆人和弗莱明人经常不得不用英语交流。(他补充说,比利时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不到总人口的1%——被称为“最后的比利时人”,夹在这个国家两个截然不同的派系之间。)他想知道,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否会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内消失,届时将没有人能将这两个机构联系起来。
也许到那时——在没有统一的比利时的情况下——分裂看起来更像Derez坚持的那样,毕竟是“典型的比利时解决方案”。
*修正:这个故事最初说祈祷书被藏在浴室里。这是一间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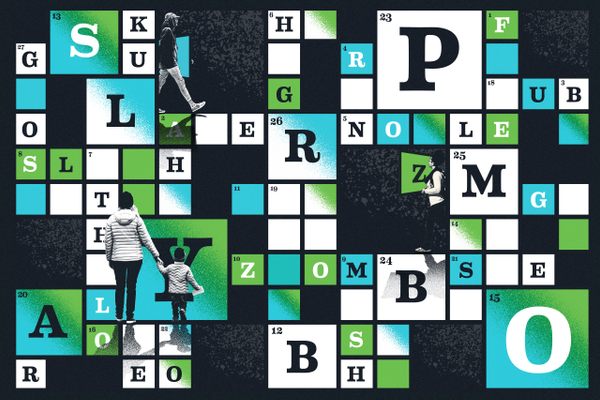











在推特上关注我们,了解世界上隐藏的奇迹。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了解世界上隐藏的奇迹。
在Twitter上关注我们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