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峰被淹没了山脉穿过孟加拉湾的表面,形成了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的572个岛屿、小岛和岩石。按照官方说法,这些岛屿属于印度但它们位于近一千英里之外。他们崎岖的雨林是150多种兰花的家园,从野生香草到红褐色Erythrorchis altissima它从腐烂的木头和树叶中吸取养分。但这些岛屿上最著名的兰花可能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兰花:h·g·威尔斯1894年短篇小说中的一种嗜血的花朵。《奇兰之花”。
像许多生长在树枝上的真正的安达曼兰花一样,这种名义上的奇怪兰花的根暴露在户外,而不是埋在土壤里。与任何真实的兰花不同,当威尔斯小说中的兰花开花时,这些空中的根茎会寻找人类猎物,并像“水蛭一样吸盘”攻击,吸干受害者的血液。就恐怖故事而言,《奇兰之花》相当平淡(兰花收藏家的管家能把他从植物的魔爪中救出来),但它是一个早期的例子,一个多世纪以来,植物恐怖小说的触角一直缠绕在人们的脑海里。这些怪异植物的故事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恐惧,并揭示了人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乍一看,植物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怪物。它们通常被视为生命和成长的象征。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英国文学教授道恩·基特利(Dawn Keetley)说,它们通常不引人注目,以至于许多人都忽略了它们——这就是它们潜在的恐怖之处。她说:“如果你看过恐怖片,可怕的东西总是来自壁橱和黑暗的角落。”“植物令人恐惧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不认为植物会构成威胁。”
当然,有些植物是有毒的,对那些吃了它们的果实、摸了它们的叶子或甚至呼吸附近的空气。几种“食肉植物通常生活在营养贫乏的环境中,进化成捕捉昆虫猎物。然而,植物恐怖并不倾向于以自然界中存在的植物为特征。相反,这一类型会衍生出一些奇幻的植物群,它们会主动寻找人类去消费、控制或征服。

可怕的植物故事的出现似乎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老神话和传说包括人变成植物的故事,反之亦然,但通常不是为了吓唬人。“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在人类和其他非人类动物之间,当然也在植物之间建立了障碍,”基特利说,并补充说,当这些界限被打破时,“那就是开始可怕的时候。”
Keetley说,最早的植物恐怖的例子之一就是人类和植物特征的混合,产生了可怕的效果:1844年Nathaniel Hawthorne的故事“Rappaccini的女儿”,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女人在照顾她科学家父亲的有毒植物花园时,自己也中毒了。
在19世纪,随着许多西方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世界,植物在《奇兰之花》等故事中变得更加邪恶。然而,威尔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吸血植物的噩梦,它的仇外殖民思维将岛上可怕的动植物作为该地区土著人民的象征性代表。
这种比喻并不是威尔斯对待安达曼群岛人的唯一方式。波特兰州立大学土著民族研究教授Kali Simmons (Oglala Lakota)说:“似乎对土著民族新威胁的焦虑经常被投射到环境上,所以环境本身成为威胁,而不是土著人民。”
在20世纪,邪恶的植物不断出现在故事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恐惧。例如,红色恐慌出现了一系列的故事,如三脚怪之日(1951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随后是1962年的一部电影)《盗尸者的入侵(1956),描绘了来自外太空或由苏联科学家设计的怪物植物,渗透到人类社会。基特利说:“它利用了共产主义的恐惧,我认为这是植物独特的另一种表现:我们认为它们没有情感。”“所以他们确实是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很好的替身,就像人们在50年代对共产主义者的看法一样,他们只是一群没有感情的人。”不像西方人善于表达和情绪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植物恐怖通常与生态恐怖的类型相吻合:现在,植物对环境破坏的反应是猛烈抨击。Keetley提到了2008年M. Night Shyamalan的电影的发生2006年的书和后来的电影废墟作为故事的例子,这些故事“将植被、植物和树木的作用与地球本身编织在一起,作为一种基本上会杀死我们的力量,而我们可能活该。”
她怀疑,最近的生态恐怖类型触及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激增的所有植物恐怖故事的根本原因:一种暗藏的怀疑:尽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与自然世界分离,但大自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我们。“我们害怕自然,我们也为我们对自然所做的事情感到内疚,我们非常确定,因为我们对自然所做的事情,它会在某个时候回来咬我们,”基特利说。
与自然世界的不安关系是植物恐怖的基础,但这种关系远不是普遍存在的。“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土著故事,无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里面都有植物恐怖,”研究恐怖中土著形象的西蒙斯说。
相反,她说,通常存在一种相互联系的感觉,动物和植物具有与人类相同的“代理和感知”。西蒙斯说:“所以我认为,对大多数土著居民来说,植物像人类一样的行为不一定是可怕的,因为植物就是这样的。”(她补充说,一些生态恐怖作品以对土著人民的有害描绘为特色:“我经常在这些表现中看到对土著人民的某种庆祝,但也不断地把我们描绘成自然的、过去的一部分,而不是文明的一部分。”)
随着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的持续威胁,对大自然愤怒的恐惧不太可能很快消失,也不太可能从西方人的心灵中修剪掉邪恶的藤蔓和糟糕的花朵。但还有一个不那么对抗的选择。
“在很多土著恐怖片中,尤其是当代土著恐怖片中,很少有关于杀死怪物的情节。这是关于所有其他必须完成的工作,以确保人们可以住在一起,”西蒙斯说。“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好吧,我们如何恢复平衡,尊重这些关系。”
Kaliyamurthy Karthigeyan是印度植物调查局的高级研究员,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研究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兰花——真正的兰花,其中没有一个吸血的——他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威尔斯曾经蔑视的土著人民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当地人完全依靠自然……不打扰自然,”Karthigeyan谈到他在那里与Jarawa、Nicobarese和Shompen社区成员一起工作的经历时说。beplay app官网他说,尽管森林砍伐和其他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同化的压力,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他们知道资源是他们的,他们的后代也需要它们,所以他们负责任地使用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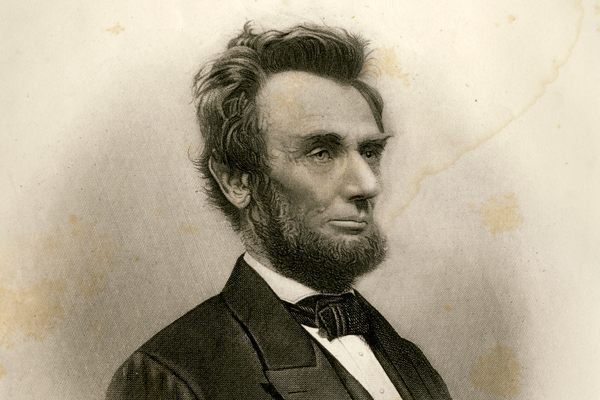













在推特上关注我们,了解世界上隐藏的奇观的最新信息。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获取世界上隐藏奇观的最新信息。
在Twitter上关注我们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