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的时候在1940年的占领期间,纳粹军队夺取了法国约80%的食品生产,其中包括约四分之一的农产品和一半的肉类。他们专注于土豆等优质产品,让法国人留下残羹剩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芜菁甘蓝和耶路撒冷洋蓟等蔬菜被贬为动物饲料,但它们很快成为法国餐桌上的主菜。
法国人靠这些耐寒蔬菜生存了9年,当1949年定量配给终于结束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蔬菜了,这并不奇怪。茄子、西葫芦和土豆又回到了市场的摊位上,但许多其他容易种植的根茎类蔬菜明显缺席,以至于几十年后它们终于开始出现在餐馆的菜单上时,它们被冠以了绰号Les lsamulisamas被遗忘的蔬菜。
弗雷德·普洛特(Fred Pouillot)是巴黎烹饪学校Le Foodist的老板,他在法国中部长大。他说,直到今天,他86岁的母亲都“鄙视芜菁甘蓝”。
她说topinambours(耶路撒冷洋蓟)是她记得在战争期间吃过的唯一好吃的东西,”他说。“但她再也没做过。”

烹饪历史学家Patrick Rambourg也有同感。他解释说:“在祖父母经历过那段艰难时期的家庭里,他们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他们只是助长了人们对占领时期一切可怕之处的看法。”
对这些蔬菜来说,战争只是棺材上的钉子。尤其是耶路撒冷洋蓟,个头小,难以削皮,吃多了会引起消化不良,就像大头菜一样,通常只有法国最穷的人才吃大头菜。
还有一些早在占领之前就被更美味的替代品取代了。当马铃薯在17世纪首次被引入法国时,有传言说它会导致麻风病和瘟疫。多亏了营销天才Antoine-Augustin有土豆的在美国,土豆后来开始取代中世纪以来欧洲防风草在法国餐桌上的位置。于是,白色的冬根开始了它漫长的凋零。
直到21世纪初,这些蔬菜才再次在法国人的心中扎根,出现在他们的菜单上。Loïc Martin是酒吧Martin和餐厅Robert的老板,他声称他们的复兴是随着“bistronomy”运动而到来的。这个词是由法国记者兼美食评论家ssambastien dsammorand在2004年创造的,指的是一种趋势,从繁琐的烹饪转向用当地产品制作的诚实的小酒馆食物。他解释说,不起眼、老式的根茎类蔬菜原来是“符合这种哲学的成分”。

再加上日本和盎格鲁-撒克逊厨师的影响,“被遗忘的”蔬菜很快就以惊人的规律出现在法国人的餐桌上。厨师兼餐厅顾问利兰·塔尔(Liran Tal)是“被遗忘蔬菜的忠实粉丝”。
他解释说:“我的菜是基于当地的时令食材,结合地中海的影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烹饪技术。”“说到被遗忘的蔬菜,我喜欢在木炭烤箱里烤大头菜或芜菁甘蓝,把它切成薄片,就像土豆片一样,用橄榄油和枣醋盛着吃。”
但这种趋势的部分原因也在于回归,不仅仅是回归根茎类蔬菜,而是回归法国美食的历史根源。羽衣甘蓝项目(Kale Project)的美国创始人克里斯汀·贝达德(Kristen Beddard)回忆说,从2012年开始,该项目试图将羽衣甘蓝重新引入法国的农场和餐桌。向当地人宣传羽衣甘蓝的历史,比向美国支持者宣传羽衣甘蓝的健康功效要容易得多。她说:“归根结底,法国人不会迷恋美食潮流。”

拉姆堡解释说,这种态度是一种更大趋势的一部分:一种寻找异国情调的态度,不是从遥远的地方,而是从家里。他说:“我们坚持与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农业有关的东西。”“吃这样的东西让人放心,因为在最近的历史中,全球环境并不让人放心。”
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食品历史学家、历史学教授肯·阿尔巴拉(Ken Albala)表示,这种对美食的怀旧远非法国独有的问题。他说:“我母亲那一代在大萧条时期长大,吃的东西都是难以形容的。”他以肺脏为例,肺脏现在在美国是非法出售的。他说:“她有点怀旧地看着那些东西,但绝不会为家人做。”即使她没有离开家去工作,她也会吃方便食品。她完全融入了现代、科技和科学,一切都是即时的。”他解释说,接下来的一代人“完全相反”,他们喜欢从酸面包到自制熟食的一切。
但阿尔巴拉认为,目前自给自足的烹饪趋势即将结束。“自己动手、手工制作、在家做饭的运动已经持续了至少15年左右,”他说。“自从第一次经济衰退以来。”他认为,我们即将迎来另一个高科技烹饪时代,就像50年代的方便食品或90年代的分子烹饪一样。他若有所思地说:“一旦这一切结束,经济复苏,我想人们又会厌倦自己动手的生活。”

在法国,钟摆可能也会摇摆,但可能不会那么剧烈。与法国的情况一样,法国的趋势更加微妙,而且往往比美国的趋势持续的时间更长。“消费者已经找到了回到农场的路,”马丁说。他不认为他们会这么轻易地把它抛在脑后。拉姆堡解释说,毕竟,尽管耶路撒冷洋蓟和芜叶甘蓝重返烹饪界已经有几年了,但人们仍然只是偶尔吃一下。“它们不是普通的蔬菜。”
“就巴黎而言,我个人认为市场上的供应非常有限,”普洛特回应道。“我总能找到红甜菜根,有点容易topinambours还有防风草,有时还有十字花科植物和水草。很少原始甜菜或cerfeuil tubereux(萝卜根的山萝卜),从来没有ficoide glaciale(普通的冰植物)或pourpier(马齿苋)。”
但即使这些蔬菜仍然不常见,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们已经成功地与困难时期分离开来,如果不是在集体记忆中,至少在个人记忆中。
“也许我们需要等到第二代或第三代,”Rambourg评论道。“我们正在远离这段历史和这段痛苦的占领历史。你知道,总有一天。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
*修正:这个故事之前说过,在美国,吃肺是非法的。出售肺供食用是违法的。
Gastro Obscura收录了世界上最奇妙的食物和饮料。
注册我们的电子邮件,每周发送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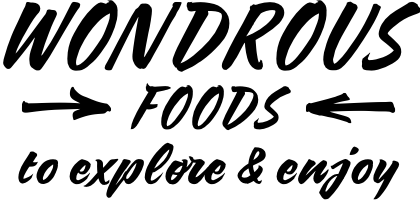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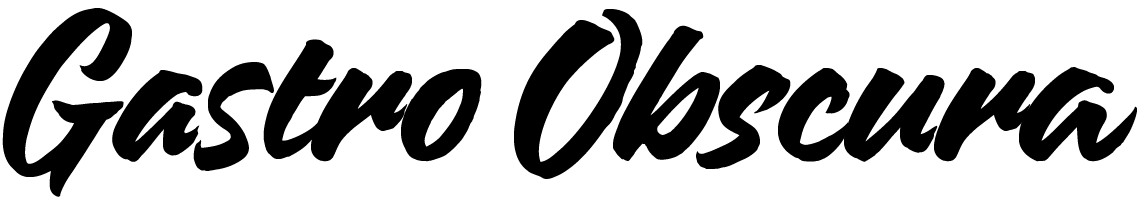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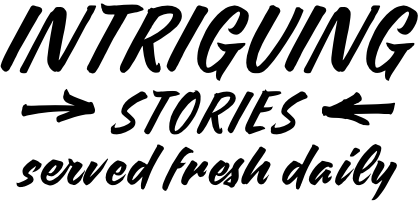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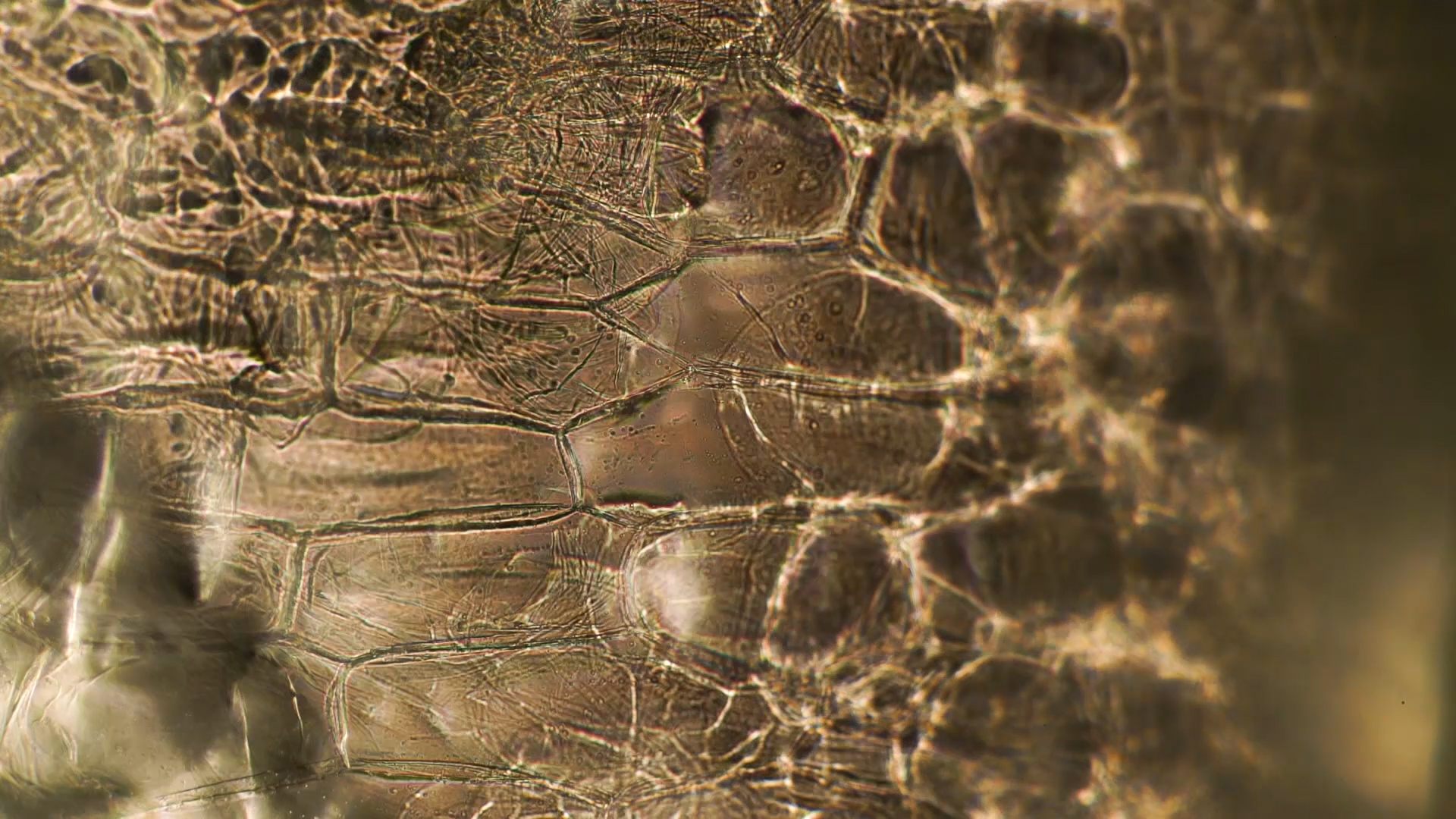











在推特上关注我们,了解世界上隐藏的奇观的最新信息。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获取世界上隐藏奇观的最新信息。
在Twitter上关注我们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