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好时代》的巴黎,a一个女人半悬在一张光滑的木床上,墙上挂着一幅老式的肖像,严厉地盯着她。昨天的衣服堆在脚凳上,从来没有打算让公众看到。我们看到的是马奈画的妓女吗?不,这里发生过暴力事件。谁邀请我们去看的?
19世纪末,巴黎警官阿尔方斯·贝蒂永设计了一套新的犯罪现场摄影系统,邀请侦探、陪审员和报纸读者进入暴力现场和从未如此赤裸裸地暴露过的私人内心世界。以前,侦探工作依赖于第一人称证词而不是间接证据。犯罪现场以素描和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警察可以用他们所拥有的材料以任何方式记录下来,没有任何标准或系统。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这种相机偶尔被用来拍摄被指控的罪犯的肖像,在贝蒂永的新系统中,它旨在引领法医客观的新时代。他的方法侧重于使用测量和一致性的可视化文档。但贝蒂永的照片所捕捉到的远不止是干巴巴、客观的描述。他们描绘了那些在暴力和痛苦中结束生命的人,营造出一种戏剧感,既是当时审美和文化转变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追求正义的手段。这些照片不只是给调查人员看的。它们最终出现在报纸上,让私人的决定令人震惊地公开。

Bertillon坚持为被告拍摄两种统一的面部照片——正面和侧面,他设计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在犯罪后使用相机。他的相机经过校准,因此,给他一张照片,侦探们就能重现犯罪现场的比例。它总是放置在距离地面1.65米的地方,平均缩小十五分之一,焦距为10厘米。从上面拍摄受害者,需要Bertillon将他沉重的三脚架和相机紧密地围绕在尸体周围。
Bertillon的方法产生的图像似乎是从鸟和虫的视角拍摄的。在一幅标题为“1914年12月9日克利希大道,卡侬先生的刺客”的照片中,一具穿着朴素的尸体上,八字腿躺在铺着瓷砖的走廊上,显眼的小胡子引人注目。通常,还会加上一个“水平面”镜头,比如在记录中记载的一位住在杜伦街的女人,名叫维芙·波尔夫人。这位年迈的受害者看起来像是在她整洁、铺陈的床旁边的镶木地板上睡着了。其他人看起来就不那么平静了:比如法拉利小姐,她的床周围是磨损的墙壁,一面破碎的镜子,她那微不足道的陶器收藏和昨晚的脏盘子。侦探的说明说她是被她的情人,一个叫加尼埃的先生杀死的。
远近各地的警察部门都热情地采用了贝蒂永的系统,这一系统帮助他们大大提高了对连环罪犯的判刑率。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是一位崇拜者;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其中一个角色称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仅次于贝蒂永的“欧洲第二高级专家”。

莱拉·格雷比尔(Lela Graybill)是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艺术史学家,她在巴黎的一家画廊里第一次看到了贝蒂隆时代的犯罪现场照片。她说,看到这些由警察拍摄的精心校准的照片摆在观众面前,“太不和谐了”。看着它们,她想起了那个时代更多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一幅画,现在叫做室内(以前称为强奸)。在这幅作品中,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在一间杂乱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摆出虚弱、忧郁的姿势,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从华丽的墙纸到萎靡不振、部分裸露的身体,它与典型的贝蒂永构图惊人地接近。观众被置于打断了一些亲密而邪恶的东西的位置。贝蒂永和德加是同时代的人。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见过面,但巴黎奥赛博物馆的一位策展人说德加的室内背叛了“贝蒂隆助理在犯罪现场的科学凝视”。

在一个文化历史文章“法医之眼与公众心理:犯罪现场摄影的Bertillon系统格雷比尔说,将犯罪现场照片归类为“一种证据形式,将其置于经验科学的领域。”beplay体育官网电脑板但贝蒂永却有不同的看法。她写道:“相反,他认为犯罪现场摄影是为法庭和陪审团的眼睛准备的。”“在那里,它将不是一种客观证据的载体,而是一种信念,甚至复仇的情感催化剂。”
贝蒂永自己曾写道,当陪审团看到谋杀现场的恐怖画面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被唤醒了一种报复的感觉,我们的准则称之为公开报复。”(直到1944年,法国才允许女性合法担任陪审员。)
暴力作为一种奇观,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出现,对1904年的巴黎人来说并不新鲜。从1871年3月到5月,一场公民起义为巴黎短暂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府公社铺平了道路。国民政府通过迅速粗暴地使用武力重新获得了控制权。“全城都有大规模的处决,”格雷比尔说。“巴黎公社及其后果得到了广泛的摄影报道。”虽然更多的是为了新闻目的而不是解决具体的犯罪问题,但这为贝蒂永的犯罪现场照片开创了先例。对巴黎公社的报道使可怕的画面成为普通报纸和杂志的常态化特征。

警方的事情越来越多地被重新包装成有趣的媒体报道。1881年,法国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犯罪报道稳步上升。警察工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摄像机,不仅捕捉到了谋杀案的受害者,而且暴露了他们家的私密环境。一般来说,在当时的法国艺术表现中,卧室往往以妓女为特色,就像马奈的作品一样奥林匹亚在这幅画中,一张凌乱的床是一个基座,上面是一个眼睛充满挑战的裸体女人,她被送给鲜花。任何拜访过法国家庭的人都会说,他们很少提供参观房屋的服务,而且会感到非常谨慎:卧室的门通常都紧闭着。当公众突然在晨报上看到犯罪现场的照片时,他们也被置于偷窥者的位置。
摄影应该比素描师更精确,比侦探的笔记更可靠,比记者的印象更不容易受到耸人听闻的影响。
然而,尽管这些努力将主观性从等式中剔除,但事实证明,摄影对主观性是敞开的。贝蒂永自己的话揭示了犯罪现场几乎被视为观众想象可能发生的可怕事情的舞台或画布:
在左侧前景中,破碎的窗玻璃、半开的窗户和被遗弃的拖鞋让我们在想象中重建了刺客们偷偷进入黑暗房间的路径。你看到他们点燃了在椅子上发现的蜡烛;想象一下,当他们发现不幸的R先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时,他们会有多么愤怒。R先生睡得像一只忠实的贵宾犬,虽然不是很警惕,但他却在大门对面把守着通道。
在一组被称为施泰因黑尔事件(Steinheil Affair)的谋杀案的照片中,格雷比尔注意到,尸体在一张照片和另一张照片之间被移动过,一根原本躺在尸体旁边的登山杖(一种带金属头的登山杖)也被移动过。顺便说一下,它只是稍微重新定位,她总结说,目的是帮助观众了解公寓的布局。“他们在创造一些叙事,不一定是恶意的,”她说。“在这里,照片不需要完全不受人为干预的影响。”
贝蒂永的遗产与我们同在。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执法部门收集面部照片和扫描身份证件时,都会感觉到贝蒂永的手。我们仍然依靠照片来描绘遥远的时事和犯罪现场。摄影作为一种纯粹客观的纪实媒介的理想也一直伴随着我们,尽管框架的界限应该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误解。过去和现在,摄影师决定拍摄对象的姿势、光线和裁剪方式,每一个决定都会改变照片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即使相机见证了所发生的事情,它也激发了许多想象的重建,解释和情感,因为有个人观众。用贝蒂永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只能看到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一个人只能观察到已经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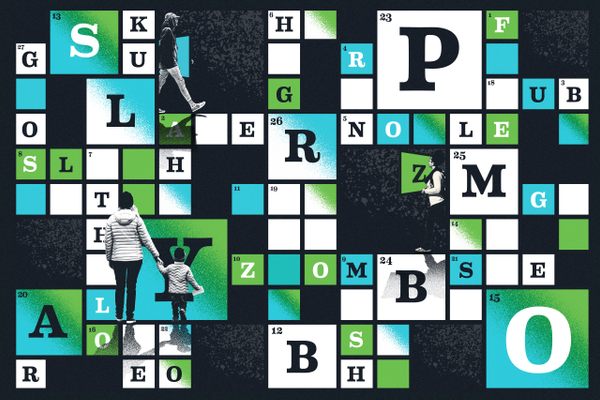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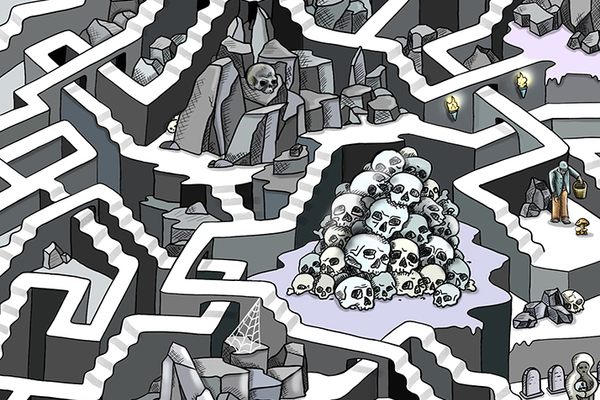



在推特上关注我们,了解世界上隐藏的奇观的最新信息。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获取世界上隐藏奇观的最新信息。
在Twitter上关注我们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